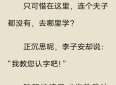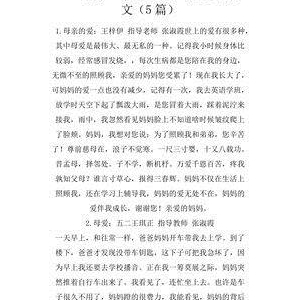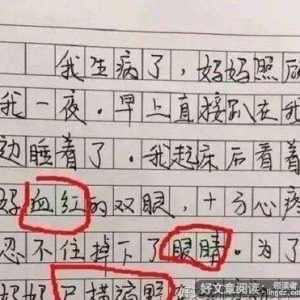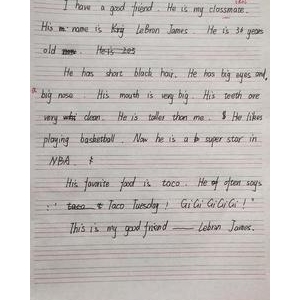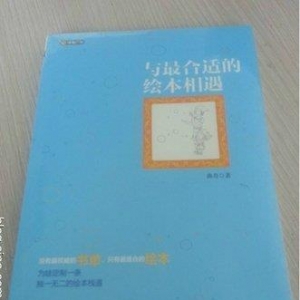我把书合上时,窗外的路灯刚好亮起来,纸页间那股淡淡的浆糊味被灯光烘得发烫。四十年,就这样被作者一页页捻开:少年想写小说,青年却进了“材料森林”,中年在“兹通知”“妥否,请批示”里拔不出脚。读到这里,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右手食指——那里有一粒厚茧,是三十年来签字、翻文件、敲键盘留下的“公章”。我忽然明白,原来我和作者隔着纸背,却是并肩的囚徒,又是彼此的放风人。
书里最打动我的,不是他写了多少篇“领导讲话”,而是他退休那天做的第一件事:把办公室最上面一格的“红头文件”全部卖掉,按斤称,换回一摞诗集。那一瞬间,他像把半生官袍脱下来,折成纸船,放进一条叫“现代诗”的河里。他说:“我终究要让句子长出肉,让标点会咳嗽。”读到这里,我眼眶发热——原来我们都可以这样,把被公文磨钝的笔,重新削成一把匕首,或者一枝杏花。
合上书,我翻出自己十年前写了一半的小说草稿,纸已经黄得像我早年的理想。我把它铺在餐桌上,像摊一张旧地图,又找出一本崭新的笔记本——第一页写下一行字:“余生请多指教,诗与小说。”从明天开始,我要给每一首笨拙的现代诗系上鞋带,让它们先跑到公众号、今日头条的广场上,哪怕只能换来零星几声“点赞”的掌声;也要让那本小说继续发芽,哪怕长出的是歪脖子树,也要在自家院角遮一片阴凉。
当然,我仍会买纸质书。电子书再轻便,也捂不热手心;而纸质书在冬夜里会自己长出体温,像此刻我手里的这本《我的读写四十年》——它把作者四十年的体温传给我,我又把它按在胸口,像按一颗刚刚复苏的心脏。纸的温度,就是人还愿意与字相亲的体温。
写到这里,夜已深,我把书插回书架,听见纸页轻轻“咔哒”一声,像关上一扇小门。我知道,门后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条暗巷——巷口挂着褪色的招牌:
“小说与诗,仍在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