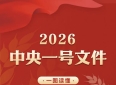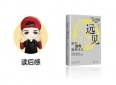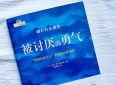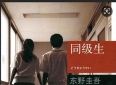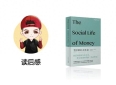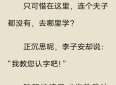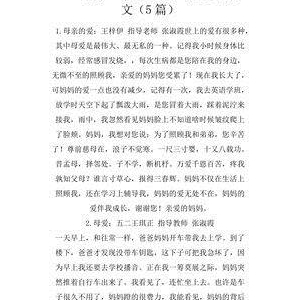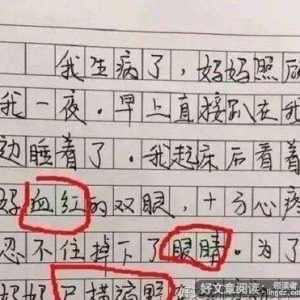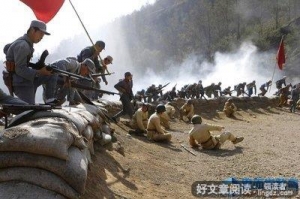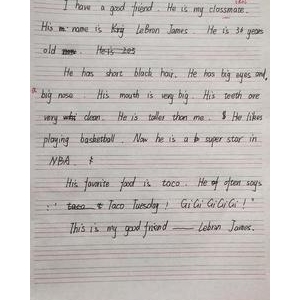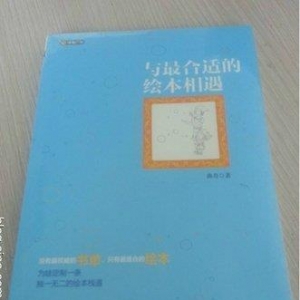《儒林外史》是一面刺破时代虚妄的照妖镜。吴敬梓以冷峻诙谐的刀笔,将科举制度下的文人群像刻画得淋漓尽致——既有范进中举疯癫的荒诞剧,也有王冕画荷守志的清白魂。读此书,既为匡超人伪善变节而齿冷,又为杜少卿散财济困而击节。那些对功名枷锁的嘲讽、对人性异化的悲悯,穿越三百年烟尘,依然映照着当代社会的精神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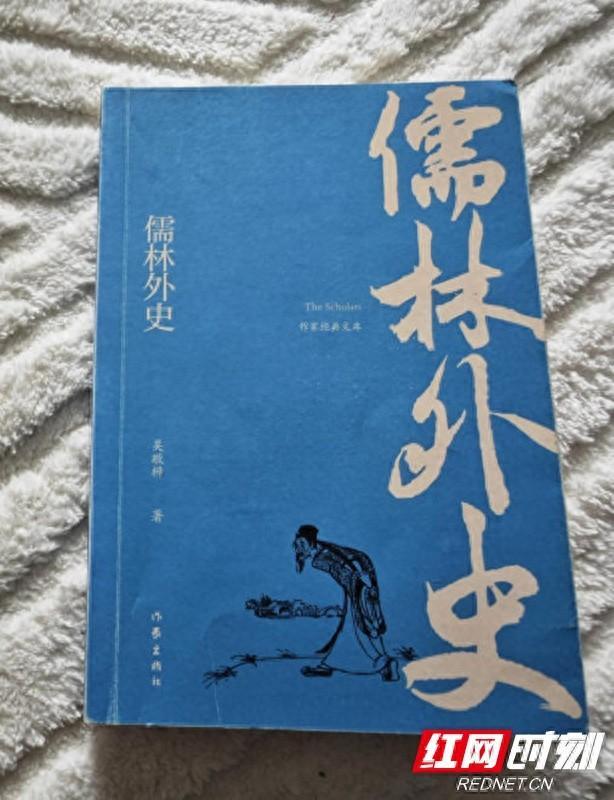
《儒林外史》开篇以一首《秦时月》定调:“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 这首词既道尽了人生选择的艰难与无常,也暗含了作者吴敬梓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沉思考。全书以 “儒林” 为镜,映照出明清士人的生存图景:有人醉心科举,以功名为终身追求;有人隐于山林,以清高自诩;有人在雅俗之间挣扎,最终难逃命运的嘲弄。吴敬梓以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 的笔触,不仅刻画了士林百态,更在雅俗的对立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命题——俗人与雅士,能否存于一身?这一问题,既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追问,也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揭示。
范进中举的故事是《儒林外史》中最经典的讽刺篇章。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中举前饱受冷眼,中举后却 “银子、宅子、奴仆” 纷至沓来。这一戏剧性转折,揭露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逻辑:功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对范进而言,科举不仅是对儒家经典的背诵,更是对生存尊严的挣扎。人生在世,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不若趋炎附势,钻营官场,以图富贵。这种现实主义的抉择,将 “俗” 与 “雅” 撕裂为对立的两极。
周进的遭遇更令人唏嘘。六十岁的老童生在贡院号啕大哭,爬过号板后竟考中举人,最终官至国子监司业。他的疯癫与执念,暴露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异化——当 “功名” 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尺时,尊严与人格便沦为可交易的筹码。吴敬梓在此并非单纯批判科举,而是揭示了制度对人性的扭曲:知识分子的 “俗” 并非本性使然,而是社会结构强加的生存策略。
与范进、周进的 “俗” 相对,王冕、杜少卿等人物则被赋予 “雅” 的象征意义。王冕以 “画梅为生,不求闻达” 自居,却在晚年被皇帝征召,最终选择隐遁;杜少卿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却在政治动荡中难逃悲剧命运。这些 “雅士” 的形象看似超然,实则充满矛盾:他们的清高往往源于对现实的失望,而 “隐逸” 本身亦是另一种形式的妥协。正如鲁迅所言,《儒林外史》中 “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皆现身纸上”,雅俗的界限在现实中早已模糊不清。
萧云仙是书中罕见的兼具理想与行动力的人物。他领兵平叛、兴修水利,试图以一己之力实现 “治国平天下” 的抱负,却最终因与世俗格格不入而被迫退隐。他的结局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真正的 “雅” 往往需要 “俗” 的支撑,而 “俗” 一旦沾染 “雅” 的理想,便又会成为社会规则的牺牲品。萧云仙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儒家 “士” 的精神困境的缩影——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的碾压下,终将被迫选择 “雅” 与 “俗” 的某种畸形结合。
吴敬梓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完全否定雅俗的任何一方,却在笔触间流露出对 “雅” 的精神追求的深切敬意。他以讽刺笔触书写范进的疯癫、周进的辛酸、严监生的吝啬,但对王冕、杜少卿等 “雅士” 的刻画,却始终暗含着一种理想主义的仰望——他们的清高、风骨与气节,是吴敬梓对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终极寄托。然而,这种 “雅” 恰恰成为他们生存的枷锁:王冕因拒绝出仕而隐遁山林,杜少卿因挥霍家财而潦倒一生,萧云仙因理想主义而壮志难酬。雅的崇高与现实的困顿形成尖锐矛盾,吴敬梓通过这种反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精神的 “雅” 在世俗社会中往往意味着物质的匮乏与命运的悲剧。
与之相对,那些投身科举、追求功名的 “俗人” 如范进、周进,尽管被讥为 “势利”“卑微”,却在制度规则下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 “成功”。这种对比并非作者对雅俗的简单褒贬,而是以更深刻的叩问:当社会价值体系将 “雅” 与 “俗” 对立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时,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便注定成为一场悲壮的殉道。吴敬梓对雅士的欣赏与对其命运的无奈交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一种复杂的态度——他既为 “雅” 的纯粹性而歌颂,又为 “雅” 的生存困境而叹息。
《儒林外史》中知识分子的抉择,实则是中国士人精神的千年缩影。李斯、陶渊明、范仲淹…… 历代文人皆在 “出世” 与 “入世” 间徘徊。吴敬梓以 “儒林” 为切口,实则勾勒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困境: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与 “风乎舞雩,咏而归” 的逍遥,始终是矛盾的两极。这种矛盾,既是个体的挣扎,也是整个士人群体的文化基因。
将目光投向现代,雅俗之困并未消解。当代知识分子在 “流量经济” 与 “清高写作” 间摇摆,与范进的 “中举焦虑” 形成奇妙互文;“躺平” 与 “内卷” 的对立,恰似明清士人 “入仕” 与 “归隐” 的现代变奏。吴敬梓笔下的儒林众生,与今天的 “打工人”“自由职业者” 共享着相似的生存困境:在制度与人性的夹缝中,每个人都需在 “俗世生存” 与 “精神追求” 间寻找平衡。
雅俗之间,何以安身立命?或许答案就藏在吴敬梓笔下的市井烟火里。马二先生游西湖时,既赏 “断桥残雪” 的诗意,又贪看 “油炸桧” 的热气;鲍文卿既能在戏班后台擦拭盔头,也能与文人共论《牡丹亭》的曲律——这些未被雅俗标签束缚的生命状态,恰似中国文人精神中那根柔韧的 “青藤”。知识分子不必困守 “竹林七贤” 式的精神孤岛,也不必堕入流量至上的媚俗狂欢,或可效仿晚明张岱 “人无癖不可与交” 的豁达——既能与老农细说稻粱,又能同高僧论辩禅机,方是 “大雅若俗” 的真谛。我们终将明白,《儒林外史》开篇那轮 “秦时月”,照见的不仅是明清士林的悲喜剧,更是每个时代寻找精神故乡的永恒跋涉。毕竟,将相神仙的冠冕之下,跳动的始终是一颗凡人的心——既要直面生存的泥泞,又渴望触摸星空的澄明。
文图/邹乐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