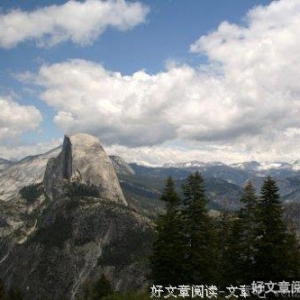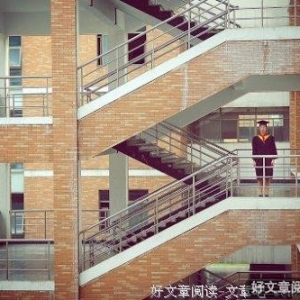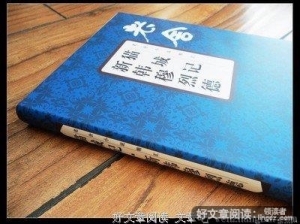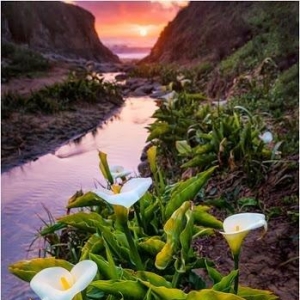作者/跃平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纳兰性德的诗句一直萦绕我心头。
年过七旬,以为岁月会教人懂得珍惜,谁曾想最后被领悟的,却是无情与冷淡。
亲情,本该温柔以待,却在晚年,如落霞般疏离;如霜雪般冰凉。
小时候,记忆里的家,是一盏灯,是温暖饭菜,是父母慈爱的微笑,是兄弟姐妹间的打闹与嬉笑。
那时候,我以为,这份亲情会像春水长流,一直滋养着彼此。
而今,年华走过了四季,才明白,有些东西,早已悄然改变。

【1】
每当夜晚降临,我坐在老屋的窗前,看着路灯下稀疏的行人。
盛夏蝉鸣几度,旧木门吱呀作响,却鲜少有人造访。
我总想起往昔那些喧闹的日子,儿女围着餐桌,呼唤我的名字,眼里盈满依赖。
可是,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各自奔向生活的远方,电话变成例行公事,祝福短信变得冷淡且客气。
朋友劝我:“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奔忙,你别太奢求。”
我无言,只默默想着杜甫那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天涯若比邻,却又隔着看不见的距离。
曾想,这就是命运的轨迹吗?亲情本应无价,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被拉扯稀薄。

【2】
我有一个朋友,张叔,今年七十二。他住在小城郊外的老宅里。
我们常常坐在院子里喝茶,听他诉说年轻时的故事。张叔的儿子在省城做生意,女儿嫁到了江南,三代同堂的景象只停留在节日团聚那一瞬。
可今年春节,张叔等了三天,儿女却因工作繁忙,只让小孙子来拿红包,匆匆说声“奶奶新年好”就转身跑开。
他嘴角挂着笑,眼神却分明带着失落。他轻声道:“做父母的,到最后,都只能学会独自承受。”
我心有戚戚焉。想起明代杨基的诗:“世间父母多无奈,不及儿女一片情。”
其实,父母的无私付出,往往成了岁月里的沉默,而晚年亲情,则渐渐变成了一种遥远的期许。

【3】
我也有过倔强。不愿主动打电话,觉得自己总是低头才换来一丝回应。
有时候想发几句问候,却怕成为孩子们生活里的负担。于是,窗前花草自开自落,屋内照片蒙上灰尘。
偶有来访亲友,总要对着空荡的屋子自嘲一句:“百年之后,人情冷暖都随风。”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戴望舒的叹息,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晚年亲情残影下的无奈和现实。
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包容、忍让,总相信血浓于水,可如今,却要学会接受情感的枯萎。
从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哀伤,不过是一种宿命轮回。

【4】
也许,现实本就充满无情和冷淡。晚年并非只有失落,也有另一种成长。
我们在寂静光阴里,可以重新审视人生,把亲情收拢在心底,也把自尊和安然留在自己的世界。
我开始明白,所谓亲情,并非完美无缺。它有缺失,有遗憾,有冷漠,有疏离。
这是生活的真相,也是生命的常态。不苛求,不抱怨,不追责,或许正是老年人最需要修炼的智慧。

【5】
雨后初晴,院子里的石榴花悄然盛放。它不需要赞美,只需静静生长。
我的老伴在厨房泡茶,远处传来麻雀唧唧。在这日常的琐屑里,我试图找回那丝安宁。
有时候,我会翻看旧信。小儿女的字迹里写着:“爸,等我有空回来看您。”
更早的一封,稚嫩又温情:“爸爸,生日快乐!”这些平凡的文字,仿佛是时光里的星点,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讽刺了人间聚散,亦是千古常愁。
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一次次失去和获得的循环,亲情与距离,始终在一条绵延不定的河床上,缓缓流淌。

【6】
与其殷切期盼,不如释然安然。人到晚年,放下执念,收起对亲情完美的渴望,把情感变成日记、诗词、茶香与回忆。
人生最大的智慧,便是用一颗宽容之心,安放所有遗憾和冷漠。
夜深人静,有风穿过门隙,带来远方的落叶声。
我给自己沏上一杯清茶,将畅快与孤独一起咽下。晚年的亲情,虽有冷淡,但还是生命不可割舍的柔软。
正如那句老话:“浮生若梦,如今已轻。”
人生是一场长途跋涉,亲情是途中一缕微光。
即使再无情、再现实,我们也要学会在余生,用宽厚和豁达,抚慰自己的心灵。

【7】
我想对同样步入暮年的人说——无论亲情如何冷淡,现实如何无情,请你善待自己。
把那些心里最柔软的温度,握在手中。愿你在诗和远方、雨打芭蕉、家常岁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分美好和安慰。
不必害怕被冷落,亲情不是我们全部的归宿。
人生七十一年,已懂得命运无常,又何须在遗憾里固步自封?下一场落花,也许会带来新的景致。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既然人生总有离别,那就学会在分离里重塑自我,在冷淡里伴着温柔,在现实里做个安然的老人。

【8】
暮色渐沉,心渐平和。无论亲情如何变迁,风雨之后,心里仍有灯火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