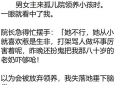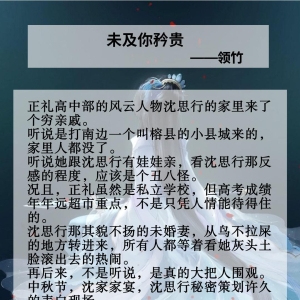「我妹是985高材生!她男友是公司总裁!我家存款过百万!」
二十年来,我姐的每一句话都让我如坐针毡。
她能把我的高考失利吹成名校录取,把月薪五千的男友夸成年入千万,就连我们合租的老破小,在她嘴里都成了"市中心豪宅"。
直到那次同学聚会,当她当众宣称我"放弃哈佛全额奖学金"时,我彻底崩溃了。
我摔门而出,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满嘴谎言的女人,早在我出走的第二年就病逝。
汇款记录里每月汇给我的2000元,整整20年。
1.十三岁那年,蝉鸣声格外刺耳。
我抱着一袋冰棍往工地跑。
父亲说今天要加班,我特意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了最贵的红豆冰,想给他一个惊喜。
我赶到的时候,父亲正悬在百米高的钢架上,朝下面的人比划着什么。
一根钢管突然从高空坠落,精准地刺穿了父亲的腹部。
工友们的惊呼声和警报声混杂在一起。
我跪在父亲身边,看着他的肚子像一颗拍烂的西瓜。
我撕心裂肺的哭喊着。
父亲的眼皮颤动了一下,嘴唇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吐出一口血沫。
母亲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盖上了白布。她站在病床前,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三天后,灵堂搭在了我们家的小院里。
亲戚们来来往往,说着千篇一律的安慰话。
母亲细长白嫩的手搭在棺木,眼神坚定,对所有人的话都毫无反应。
「小雨,让爸爸安心走吧。」
姐姐从背后抱住我,她的手臂勒得我生疼。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又扑到了棺材上。指甲在漆黑的漆面留下一道道带血的抓痕。
「他不是爸爸!不是!」我尖叫着,挣扎着想去碰父亲的脸。
姐姐的眼泪滴在我的后颈,反复着呢喃着我的名字。
下葬那天,烈日当头。
我看着父亲的棺材缓缓降入土坑。
母亲自始至终没有掉一滴眼泪。她站在墓穴边,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
葬礼后的第三天,我们在村口的湖里找到母亲。
她穿着绿色碎花连衣裙,在水面上静静漂浮,黑发像水草般散开。
十七岁的姐姐一手操办了第二场葬礼。
她像突然长大了十岁,接待吊唁的亲友,安排丧宴,结算殡仪馆的费用。
当夜深人静时,我能听见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发出细细哭声。
工厂的赔偿金是在母亲头七那天送来的。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递给我姐姐一个鼓鼓的牛皮纸袋和一本暗红色的房产证。
姐姐接过那些东西时,我看见她单薄的肩膀颤抖着。
她转身对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用袖子擦了擦我脸上的泪水。
「妈妈没有抛弃我们,她只是去陪伴爸爸」
「就像姐姐会一直陪着你」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母亲头七刚过,两个舅舅就迫不及待地登门了。
「小晴啊,你爸这赔偿金到底有多少?」大舅搓着手,眼睛不停往屋里瞟。
「你们姐妹还小,这钱得有人帮你们保管」
二舅直接掀开了床板。
「房产证放哪儿了?老房子得有人照看,你们小姑娘家住着不安全。」
我缩在姐姐身后,看着她挺直了脊背。
「工厂赔了一百万,钱都存在银行里。」
「房产证在律师那儿,说要等小雨成年才能过户」
她的谎话说得那么自然,连我都差点信了。
其实那个牛皮纸袋里只有三十万,已经被姐姐缝进了我的旧棉袄里。
「一百万?!」
两个舅舅同时倒吸一口气,眼里的贪婪藏都藏不住。
那天晚上,姐姐在饭桌上摆了一盘腊肉炒笋干,这是母亲生前最爱吃的菜。
两个舅舅的筷子在盘子里打架,油星子溅得到处都是。
大舅嘴里塞满食物,说的含糊不清。
「你们搬去我家住,钱我帮你们存着,每月给你们生活费。」
「去你家?」
二舅摔了筷子。
「你那破房子还没猪圈大!小晴,带着小雨来二舅家,你二舅妈正好能照顾你们。」
姐姐放下碗筷,声音轻得像片羽毛。
「我和小雨哪儿也不去。」
「不过,等小雨出嫁了,谁对我们好这钱就给谁。」
两个舅舅的眼睛同时亮了起来。
从那天起,我们家突然多了许多"亲人"。
二舅妈每周都来给我们洗衣服,大舅时不时拎条鱼来。
表姐们突然对我亲热起来,非要拉着我去镇上买头绳。
姐姐晚上给我擦头发,手指温柔地穿过我的发丝。
「你要记住,除了姐姐,谁的话都不要全信。」
她把存折藏在了我的课外书封皮里,房产证用油纸包好,塞进了灶台的砖缝中。
姐姐出嫁那天,山里的雪积的半米高。
3.她穿着借来的红色棉袄,像玩偶兔子被按在镜子前梳妆。
大舅收了三万彩礼,笑得见牙不见眼。
「小晴有福气啊,张家在镇上有两家铺面呢!」
二舅妈往姐姐头上插着俗气的金簪,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姐姐抹口红,艳得像血。
我蹲在门槛上哭,姐姐冲我悄悄摇头。
深夜,当所有人都喝得烂醉时,姐姐撬开了后院的锁。
她脱下嫁衣,露出里面早就穿好的旧校服,从床底下拖出准备好的行李。
拉着我钻进后山的竹林。
雪打湿了裤腿,我们在月光下狂奔。
姐姐的背包里装着缝有存折的棉袄、房产证,还有一张父亲母亲年轻时在省城的照片。
「我们去哪儿?」我喘着气问。
「去爸爸妈妈相遇的地方。」
「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天亮时,我们搭上了去省城的早班车。
姐姐把我的头按在她肩上。
透过车窗,我看见太阳正从山脊线上升起,把姐姐的侧脸染成金色。
4. 省城的霓虹灯晃得我睁不开眼。
姐姐在城中村租了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墙皮剥落得像老人斑。
她从行李中拿出一条崭新的连衣裙和一个小皮包。
她对着裂了缝的镜子涂口红。
「从今天起,我是来省城投资的林小姐,你是我的远方妹妹。」
她转身时,整个人都在发光。
微卷的长发,精致的妆容,连走路的姿态都落落大方,像个真正的富家女。
而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像只误入天鹅群的丑小鸭。
「为什么我要穿这样?」我揪着校服下摆。
姐姐蹲下来与我平视。
「因为你要去最好的中学,而姐姐需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有这个资格。」
她牵着我的手去了校长办公室,说她是省教育厅厅长的侄女。
校长满脸堆笑着接待我们。
我狐疑的看着姐姐,纳闷我们什么时候认识这么牛的人物啦。
我稀里糊涂的去上学,每天担心姐姐的身份会被人揭穿。
我的新同学都住在有电梯的公寓楼里,他们的父母开着轿车来参加家长会。
而每当有人问起,姐姐都会优雅地微笑。
「家父做进出口贸易的,常年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