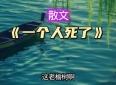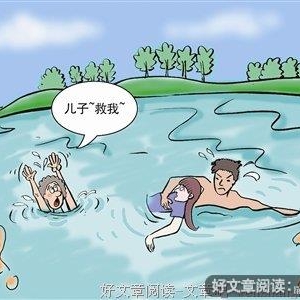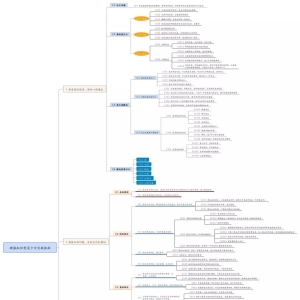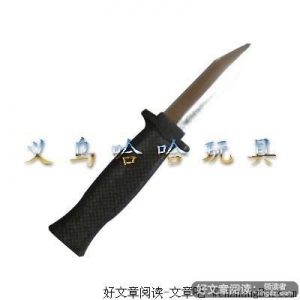晨光里的约定
凌晨四点半的老城区,巷口的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王建国蹲在早餐车后揉面,面团在他掌心反复翻转,带着规律的“砰砰”声。妻子刘梅正往保温桶里码包子,指尖被蒸汽熏得发红,却没停下手里的活计。
“隔壁老张说,那间门面下月初就能腾出来。”王建国突然开口,额头的汗珠滴在面团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刘梅的手顿了顿,抬头看他,眼里藏着期待,又带着点怯意:“真要盘下来?咱这身子骨……”话没说完,就被王建国打断:“你忘啦?年轻时你说过,想有个带玻璃窗的铺子,能看见街上的人来人往。”
八年前他们刚摆摊时,推的是辆掉漆的二手三轮车。冬天最冷的那几天,刘梅裹着两层棉袄还冻得发抖,王建国就把唯一的棉手套摘给她,自己揣着冻裂的手揉面。那天收摊时,刘梅攥着皱巴巴的零钱说:“等以后有了铺子,咱安个暖气,再也不用遭这罪。”这话,王建国记了八年。

寒冬里的坚守
去年冬至刚过,寒潮来得又急又猛。刘梅在结冰的路面上摔了一跤,尾骨骨折的诊断书递到王建国手里时,他的指节捏得发白。
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刘梅摸着腰间的止痛贴红了眼:“建国,咱别折腾了。我这腿好了也干不动重活,守着这车摊,够吃够喝就行。”王建国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攥得更紧。那半个月,他一个人扛起了所有活计:凌晨三点爬起来发面,天不亮推着车出摊,中午赶回家给刘梅擦身喂饭,下午眯两个钟头又接着准备第二天的馅料。
有天清晨,刘梅隔着窗帘看见丈夫在寒风里弯腰捡掉落的包子,后腰的旧伤让他直起身时疼得龇牙咧嘴,却还是把捡回来的包子仔细擦干净,放进了捐赠箱——那是他们每天留给流浪老人的份额。她悄悄摸出藏在枕头下的存折,那是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第二天一早就催着王建国去了中介所。

霞光里的模样
秋分那天,“建国包子铺”的招牌终于挂上了门楣。红底黄字的牌子在阳光下亮得刺眼,王建国特意请人在玻璃柜里隔出一小块区域,摆上了刘梅年轻时绣的牡丹图。
“你还记得不?当年你卫校没念完就嫁了我,总说要是学了裁缝就好了。”王建国擦着新添置的缝纫机,这是他用第一笔铺租结余买的。刘梅笑着点头,手里正给熟客改着裤脚,针脚走得又匀又密。每天收摊后,铺子就成了她的小天地,常有街坊来缝补衣裳,她从不收钱,顶多收下对方带来的一把青菜、几个橘子。
傍晚的霞光穿过玻璃窗,落在王建国刚换的发酵机上。刘梅数着当天的收入,忽然指着账本笑出声:“你看,今天比昨天多卖了十七个肉包。”王建国抬头,望见妻子鬓角的白发在光里泛着银辉,像落了层细雪。他想起二十年前在出租屋里,自己攥着她的手说“以后要让你踏实过日子”,那时的话混着煤烟味,如今竟真的在升腾的蒸汽里,酿成了最实在的甜。
原来中年人的梦想从不是什么壮举,不过是让日子像刚出笼的包子,带着暖人的热气,一步步朝着更安稳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