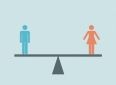这次「一封信」的主题是「友情降级」,我们一共收到了243封来信。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关于疏远与告别的故事,证明这并非个体孤独的偶发经历,而是一种时代下群体的共同体验。
曾经有些时候,我们一度相信,有些友情能抵挡时间,有些承诺能贯穿一生。直到某天,友情降级的出现,让原有的关系模式难以继续下去。它可能发生在一次至关重要的竞争之后,嫉妒的毒刺悄然埋下;可能发生在人生阶段错位的瞬间,比如升学或是婚姻;可能发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里,当你需要全力应对家庭的危机,她却已无力回应你的呼救;也可能发生在地理位置的遥远间隔中,共同话题像燃尽的篝火,只剩冰冷的余烬;它甚至可能发生在一顿期待已久的饭局上,相对无言的沉默震耳欲聋。
这个过程里,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正式的告别,只有消息回复得越来越慢,见面次数越来越少,分享欲逐渐消亡。最终,在一次心照不宣的沉默里,或是无法被看见的愤怒或是失望里,一段关系完成了它的「降级」。
我们为此困惑、自责、痛苦、惋惜,并最终在反思中完成对自己的重塑。这五封信,是五份珍贵的情感样本。它们来自不同的生命轨迹,年龄不同、性别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却共同记录了一段亲密关系如何从炽热走向疏离,记录了下沉那一刻的刺痛与浮起之后的释然。
这些故事不仅仅关于「失去」,更关于「见证」。它们想告诉我们:那些共同渡过的河流、一起铸造的剑、彼此交换的梦想,即使最终沉入水底,也曾在生命的某一刻,映照出最耀眼的光亮。
以下是关于「友情降级」的五封信。
策划|《人物》编辑部
✉️
第一封信
人物:
你好。
关注了你很久,却没想过投稿。这次看到「友情降级」这个话题,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很多话要说,便心血来潮编辑起这封邮件来。
《我的天才女友》这个故事我想看却不敢看,因为每次看到都会想起自己的「天才女友」。
20年前,我在当时住的小区里认识了她。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直到现在我依然感怀那段岁月。我们每天在小区里跑来跑去,在墙上涂鸦,揪狗尾巴草,看动画、搭积木、过家家、写故事。她每年都给我写贺卡,我也会买玩具送给她。现在我还存着当年我们交换的邮件,来来回回上千封,不知藏了多少秘密。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人可以取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只有她理解我的文艺梦,只有我欣赏她不凡的才华。我以为我们会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但美好背后藏着一颗有毒的种子。小时候,我有一门热爱的特长,无论在学校还是社区,我一直以擅长此事著称。谁看到我做这件事都会夸我做得好,我也一直洋洋自得。从小到大,成为这项技艺的行家,一直是我的梦想。
但是遇到她之后,事情反转了。她让我明白,在这件事情上,居然还有人比我做得更好。我们才刚上小学,不存在「坚持」、「努力」一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天赋」。
我们固然是最能互相理解的人,但也因为喜欢同一件事情,难免暗暗竞争。这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敌蜜」吧。
那时的我,总为自己没有她的才华而痛苦。无论我多么用力,都无法赶上她随手做出的成就。她不经意间微妙的优越感,也一直暗暗刺痛我。小学时我还想超过她。上中学之后,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学习吸引。我们不在同一学校,不能直接对比排名,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默契,不提联考成绩,只是大概透露着自己平时能达到的分数和状态。我们互相打气,每天一起学习和打卡,花很多时间聊天。那时候我在学校里没有深交的朋友,她是我最大的友情支柱,但也是我最怕被超越的人。那种既互相支持又暗暗竞争的状态也许很多人都经历过。
但是中考成绩是隐瞒不了的。在那成绩的竞争中,我「输」得很惨,以几十分的差距上了比她低几个档次的学校。
那时我也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特长不如她,学习也不如她。又因为她在特长上似乎是凭借天赋而不是努力,所以我一直在逃避那项特长。「既然有人一出生就得到了我要花十年努力才能得到的东西,那努力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放弃的话,就不用再面对才能的差距和无力感了。
无论何时看到她做出的成就,我都为之惊叹,并感到刺痛,不敢面对自己的平庸和愚拙。这件事把我压得喘不过气。为了逃避对比的伤害,我把特长丢在一边。那正好是高中最紧张的时候,所以我更无心顾及什么业余爱好了。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这段关系是如此病态。但当时我们还是拿对方当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在精神上非常默契,我们欣赏和喜爱的东西,一般人都不理解,所以那时惺惺相惜。
高中时她终于向我透露了她的困境。那时我才知道,在我看来是「完胜」于我的她,居然有各种我想象不到的烦恼。
她怨恨自己不够受异性欢迎,嫉妒学校里受欢迎的人,总是向我埋怨她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想起自己从小到大被异性追求的经历,闪过这样的念头:她怨恨的人里,难道也有我吗?我不也符合她所怨恨的特质吗?然后又觉得自己太自作多情。那时我并不能理解她。她拥有那么多我想要的东西,可是她一点都不知道。
关于异性的烦恼持续到大学。我们都一直单身,在这件事上也算是伙伴了。那时候我们交流的话题多半集中在这件事上,会一起骂身边和网上的「渣男」,互相吐单身的苦水。那时候跟她说话还是很开心的。可是后来,我又感到一层微妙的东西。我可以留学,但是她没有同样的条件。她会用「怨恨」的语气对我提起身边的「有钱人」,说他们怎样吃穿用度。于是我算了算自己留学的费用,心想:她痛恨的「有钱人」里,也有我吗?然后又觉得自己自作多情了。我想,我在她心中毕竟是特殊的,她不会恨我的。
后来,我们依然每年假期见面。见了面,依然去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但是,我们聊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厌男」和「恋爱」,似乎只有在这件事上,我们才有共同语言。她再也不跟我聊文艺,也从不问我生活的细节:学校怎么样,同学好不好,以后打算怎么办。如果我开启话题,她简短回答之后便是沉默,永远不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又过了很久,我谈了恋爱。我本以为这没什么,但是她之后再也没跟我说过话。那时候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段延续二十多年的友情,是该结束了吧。
又过了很久。有一天,我在社媒上发现她拉黑了我。我想我知道是为什么。那时候我已经明白,也许她一直都像我嫉妒她一样嫉妒着我,只是我们嫉妒的方向不一样。但那时候我已经打算从嫉妒的心态中摆脱出来了。于是我也删除了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心中竟没有波澜。
那之后,我重新捡起小时候因为她而放弃的爱好。没有了和她的「对比」,我有种解脱的感觉。然而我发现,就算我曾经擅长此事,经过多年的逃避,也已经生疏了。我必须像初学者一样,从头学起。成人的我终于懂得,「天赋」终究比不过坚持。
于是我暗下决心,坚持自己所好,珍惜自己所有,再不与人相比。
谢谢你听我说这么多。
M

图源剧集《我的天才女友》
️
编辑部回信
M:
也祝你好。下定决心提笔之前,我看了两集《我的天才女友》,画面里的莉拉和莱农正是十几岁的样子,像两只咋咋唬唬的小刺猬,一边软软露出肚皮,抱在一起,另一边又随时准备着、骄傲着也心虚着,就趁对方最不设防的时候扎你一下——不伤人,只刺挠。
你讲了她的很多事,她的天赋、她微妙的优越感,她的「怨恨」,还有她的拉黑,听起来确实很受伤。可我也因此很好奇,这么多年来,吸引你持续和她保持联系的动力是什么?或者说,她身上那份闪闪发光的动人之处,又在哪里?我想,用兴趣一致、「相互打气」和「友情支柱」来解释,大概是不够的。
很遗憾,这一封信读完,我还是不太了解你的「莉拉」。如果能回到所有的这些复杂情绪诞生之前,回到你们那些真正快乐的、在小区里跑来跑去的日子里,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又如何向彼此第一次伸出了手?这一切一定发生过,也许是后来太过于翻涌的情绪掩盖了它。
你也写过你的「自作多情」,还有她的并不知情。这也许和你们地理意义上的渐行渐远有关,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沉默同时出现在了两个「最好」的朋友身上:她没有在抱怨他人时体谅你的感受,你的疑惑也没有问出口。后来,你们两个的聊天限制在了更小的话题上,并且在谈恋爱后,似乎就悄无声息地断了联系,直到你在社媒上发现自己被拉黑。你们不约而同选择了保护自己,却也因此形成了隔阂,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里,作者西蒙斯就专门指出,「沉默相待是绕开正面冲突的捷径」,但沉默也剥夺了自我表达和主动解决问题的机会。
其实在人与人相处时,不同甚至分歧实在是太常见了。这背后的道理也再简单不过: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没什么关系,那我何必让着你?可问题就在于,我们是朋友,是彼此在乎的存在。不同和分歧存在没问题,更重要的,也许是彼此想要理解和靠近的心。在关系中,爱之外的东西可以很多,但爱也要很多很多。
当然啦,别看絮絮叨叨这么多,这么多年来,我也搞丢过不少朋友。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些关系确实存在阶段性。你说她拉黑你时,你心中已没有波澜,也许,这正说明你们的关系已经走完了它的旅程,这没什么问题。
至于那些拉扯的,放不下的——在25岁之后,我慢慢学习硬着头皮问出口一些有些蠢笨但真诚的话。「你是怎么想的?」「你的话让我有些伤心,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我有哪些你觉得不妥的地方吗?」还有「我错了,我很想你。」但说实话,放在十年前,我真的讲不出来。青少年时期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气让我拉不下脸,也意识不到真正的友谊应该如何维护。可年少时没学会处理这些比较,很正常,也不是任何人的错。
我想,真正的成熟,也是学会接受我们在过去和当下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天才女友这种叙事的迷人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能看到另一种活法的可能性,但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路有千千万,能支撑我们生活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必须要成为谁、踏上某条唯一的路才能得到的。去珍惜已有的、去坚持所爱的,去学会在新的关系里给予与接受,才是那些思考最终应该抵达的地方,而通过这封信,我能感觉到,你已经在这样做了。
那就祝你和她未来都更好。
阿宁

图源剧集《我的天才女友》
✉️
第二封信
尊敬的人物:
在工作的间隙看到你们的推送,关于「友情降级」这个话题,我想和您们聊聊。
在我的生活中,「友情降级」是在恋爱后以及进入婚姻后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大学时期,就算当时在恋爱状态,与朋友的交往还是很密切的,放假回家,以及过年过节还是会团聚,后来大家考研、参加工作,慢慢被琐事填满,朋友之间聚得越来越少。
我在26岁时进入了婚姻,和老公的生活非常稳定,下了班之后我会回家做饭,老公每天也会按时回家吃饭,做家务,我觉得婚姻生活很充实,这是我喜欢的生活,慢慢淡出了以前的社交圈。好几次看到贵栏目的推送,有关于已婚女士没有朋友,又或者是现在的友情降级这类话题,我慢慢意识到,我和我的朋友们也渐渐失去了以往的感情。
我学生时代的朋友们比我「慢热」。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向往爱情,爱结识朋友,可在当时我的朋友们就显得比较宅,不爱聚会,更别提恋爱,就这样我成为了我朋友圈里恋爱史较丰富,然后最早结婚的人,让我没想到的是,如今我的朋友们就变得和我十年前一样,爱聚会,爱拍照,爱逛街,而现在的我早已放下了躁动的心,下了班只想回到自己的小家,手机里也很难有一张精修照片。
如今我很少去聚会,更爱陪伴家人,发现与学生时代的朋友们越来越没话聊,有时发送一条微信过去,很久才有回复,他们跨年聚会这些也不会再喊我。只是想到最要好的她们,还是会想说主动联络,或者身边有不错的人可以介绍给她们认识。现在能聊得来的朋友是工作之后结识,和她们吃饭聊天,不会冷场,互相可以get到点,虽然和青梅竹马的同学们少了一份熟悉,可我还是开心的。
「友情降级」这个事我看得比较开,因为这里面肯定是有我自己的原因的,但这也是我主动选择的,有了工作、稳定的伴侣后确实匀给朋友的时间在变少。人类的悲喜各不相同,我也觉得成年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舒服就好。
莉莉

图源剧集《老友记》
️
编辑部回信
莉莉:
你好!
读完你的来信,很羡慕你的洒脱和坦然。确实如你的感受,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心气儿,或许和性格有关,或许和成长有关,或许和境遇有关,一群人一起走,难免有错位的时候,只要主动选择了自己舒服的生活状态,就挺好的。
想了想我自己,更像你的那些「慢热」的朋友,在人生的各个时空都显得呆滞又迟缓,至于结交朋友这件事,全得感谢对方朝我走出的那一步,以及日后的不弃之恩。到现在,熟悉的几个朋友,都基本一起走了十几年的路,而很难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新朋友,也是因此,无形中有很多错过的、淡出生命的遗憾。
看来,不管是开朗热情的人,还是内向迟钝的人,「失去」都是难以避免的。
不过,之前在网上看到一段话,很可爱,说:我煮泡面的方法是高中的一个朋友教我的;我每年秋天听的歌单,来自我曾经不惜开车越过边界也要去见的男孩子;我爱吃寿司,因为一个已经和我绝交了的女孩当初极力推荐我尝试;我爱吃印度菜是小时候和好朋友出去玩时她父母随便给我点的;我爱看某部电影是因为以前和喜欢的人一起看过……我是我爱过的每一个人拼成的马赛克,我的每一拍心跳都有它的来处。
确实,如果分开是不可避免的,那共同走过的路就是相遇的全部意义了吧。每个人都只能带着那些留在彼此身体里的、影影绰绰的印记,继续走新的路,遇见新的人。想到那些弄丢的朋友,再想到这些,会觉得是一种安慰。
想起今年夏天一段突如其来的、矫情的经历。当时去了趟山西,从晋祠博物馆离开的时候,要穿过漫长的小路,风把裙摆吹到腿上,一个人撑着伞往停车场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得心都要碎掉了。
晋祠是一个许久不联系的朋友在许久前推荐的,去了,果然很精彩,彩塑、建筑、石刻俱佳,穿行其中,像一场漫游。那天站在圣母殿抬头看时,丰富到眼睛和呼吸都不知该落在哪里。或许是很多人都有的一种感受吧,在巨大的震撼和感动面前,会生出难以言说的孤独感,世间无人可以分享的那种。于是一瞬间突然想到了那位朋友,心想,如果当时同在就好了。
淡出彼此的生命和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觉得没什么可留恋的,也没什么可遗憾的,过去就过去了。还是第一次,有种强烈的失去感,或者痛感。
如果是弄丢一个漫不经心的恋人,不过是弄丢一段情感或者一段时光,就像掉了头发,再严重些,掉了指甲,而已了。但弄丢一个合拍的朋友,或许像是整个与之相关的自己都被劈开,然后焚掉一半。
今天读完你的信,瞬间又想起了那一刻。不太想说什么「向前看」,但想俗套地说一句「珍惜」。我们会有很多新的际遇,很多探索和好奇,但是路那么长,说不定还风大雨大,要是能和遇到的朋友同行得长一点,是多幸福的事啊。
几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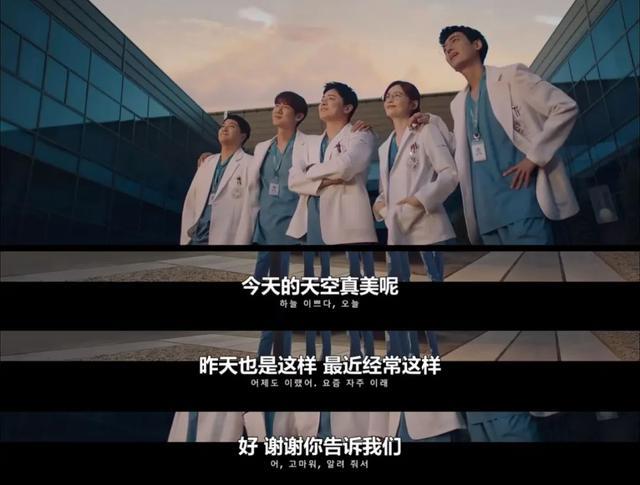
图源剧集《机智的医生生活》
✉️
第三封信
人物:
我是主动降级的,对方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完成了曾经高亲密情感关系死亡的痛苦,感受上人生重要角色的断裂失去,以及逻辑层面在道理上的自洽。从意识到,痛苦,到接纳,适应和调整完毕。在三到五天内,已经开始现实的行动终结和哀悼,感恩,祝福,离开原来的位置,到了新的关系角色坐标。
我们是2024年的5月相遇的,在一个艺术疗愈的活动,起于我看到了她的痛苦,主动回应发言,而她出于一些实用性的需求,活动后主动跟我联系,微信的对话沟通中,我感受到自己被清晰地欣赏、看见,以及她当时与我链接的热情。
后来我们偶然地一见再见,她很主动地约我,我们见面聊天,意外发现很多相似,颇为一见如故。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们频繁而密集地出现在彼此的生活中,互相支持、陪伴,参与对方的当下和畅想的未来。我们经常见面,一起吃饭,互相会偶尔住到对方家里,第一时间陪伴彼此在工作事业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在一次次深夜对话里看见对方原生家庭里的创口,了解对方的人生轨迹和重要人际关系的经历,见证彼此因为和喜欢的男生互动而状态高高低低,互相发自内心地许愿想要成为对方的支柱,两个独自在大城市漂泊成长的女性互相抱团,看见和接住对方。
我们其实是性格很不一样,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很不同,处事方式也有许多截然不一样的人。但是在高频的见面、联系、互动中,尽管也闹过矛盾,但双向奔赴的及时沟通和维系关系,让我们越靠越近。
去年年底,我们一起合作了一个播客,叫「浪蔓的诗」,结合了我们的名字以及我所寄托的关系期许。我在我们经常见得到面的那半年里,几乎每一次,对我来说有所触动的节点,我就会写很长的朋友圈,表达我的情绪和感受,歌颂和表白我们的情谊和关系。而那时候,我们的关系,时常成为我感恩和感激的主题,很多次和她的相处经历,都会让我感觉,像是上天给我带来的生命的礼物和奇迹。
去年年底,她突然选了一份在上海的工作,拿到offer之后打电话给我。我当天晚上接到电话之后,从开始默默流泪,到特别伤心难过的流泪,不可抑制地难过了十几分钟,后来断断续续地,哭了半个小时。我觉得真的太难过了。当时还很信任和亲密,觉得不能自己默默哭,马上打视频给正在回杭州的她。给她看到了我多难过,一边哭着,一边说着一些话,碎碎念在表达我的想法。她跟我说上海不远啊,和杭州很近,她只是去了另一个城市,又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我不用那么伤心难过至此。
而她是在大概一个半月余之后,因为工作压力累积,以及其他生活方面的不顺,情绪累积到了一个让她感觉躲无可躲的糟糕地步,她哭着找我视频,说终于意识到不同城市带来的差异。见不到我了,无法打个车就看到我,无法那么及时和详细地分享了,那种有承载的安全感和各种情绪的流动和出口没有了。她终于意识到了,因为她实际的感到痛了。
很多的东西,在相隔异地的话语里是有尽头的。更何况对于一个语言表达习惯跟我很不一样,相对来说语言没有那么详细和细腻的人而言。那么,我们的关系,一定会有改变。关系会较之前逐渐走疏远,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的情绪和感受,第一时间,在面对这种亲密到疏远的改变时,那些情绪,从眼里,流出去。
2025年初始,我的母亲癌症晚期复发,我在主动和被迫夹杂中突然地离开了杭州,回到了家乡。单亲家庭,独生子女,我一直和妈妈共同生活。我离开我熟悉的,成年毕业后的那个我所构建的一切,回到我原生家庭所在的环境,回到我18岁以后就在选择远离,步伐一直在向外探索的出生地。我的每一步,每一个面向,都被生活拉到新的极限,混杂着诸多的实际生活事项的处理和庞大关键的决策问题,从没有喘息间隙地,没有预告地同步朝我砸过来。我曾陪母亲经历过重度抑郁的7年,而这一次,我又再次仿佛献祭自己,去陪伴,去负责,去处理,同母亲一起,去面对更加急迫和极限的生命危机。
在做这些时,我自己好像是到最后一位。我的生活起居和一切,所有的实际生活、关系、自我都在崩碎,我一步步让渡着曾经的自我。这大半年,我一边每天爬起来去面对处理,一边觉察自己持续在消耗而无法破局的生命力,也完全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在许多的事情上,我好像有其他选择,但是实际上我也别无选择。大半年里,每次都是以我最重要的妈妈的生死为代价的大小决策和场景,许许多多的事情,我都在独立去处理和面对、承担。
而她,只在过年的时候,来看望过我一次。我带她去我家吃年夜饭,她知道我的情况,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到江浙沪,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她来看我,同时旅游。之后我们就一直线上联系,再也没有见过面。
今年6月,意外而突然地,我的妈妈离世了。她是第一个,敏锐地觉察到我或许会很责怪自己,责怪到会不想继续我自己的生命。隔着屏幕,在得知这件事情后,第一时间跟我说,「不要太责怪自己,你真的真的已经尽力了」,她说回江浙沪吧,我们互相照应。她想念我,需要我,叫我不要死。在那之后,我几乎完全失去了主动跟她关切和维系关系的主动性,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已经崩溃垮掉了,我没有任何多的力气,去再更多地维系线上的远程的友谊,我没有那么多地主动发消息或者发起视频。
我一直在面对和处理,母亲离世过后这个破碎的自己,这个耗竭而崩溃的,不知道这个世界和我还有什么连接的自己。我主动地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我一直在给自己找活下去的羁绊理由。庞大的无意义感和疲惫,像是抽空了我的生命力,光是保持自己活着就觉得很费力了。但是我也一直努力好好照顾自己,我知道这是阶段,这是必经,我相信这不是我的终局。
回杭州安顿后,我一直在尽力地照顾自己,没有力气社交,没有力气离开小区远一点去出行。她在7月中旬就和我说,主动和我提,7月底来杭州见我,住我这两天。然而事态很快发展成不见面,我们礼貌但不愉快地结束了对话。那天开始,我连着两天,身体都很难受,像又被抽走了什么的,留下一个失去了重要核心支撑的空洞。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糟糕的躯体反应,浑身无力,头重脚轻,眼神极其疲惫,从沙发上坐起来,下楼丢垃圾,对我来说仿佛要长征千里。从上午,到下午,到晚上,我一直在努力积极地采取一些行动,我想救自己。
接下来,我做了很多细小的、迅速的反应,一步步地在每一个当下的瞬间,去做一些行动,找到可用的支撑,去度过一个个瞬间,逐步完成了我要做的给自己充电的事情。面对未知的新情境,也参考我已经知道的对自己的了解,幸运的,跋过未知的躯体反应的山,涉过熟悉的情绪反应的水,度过了这两天,逐步回血。
对我来说,是一步步的累积,在很多次的相处对话里,我对这段友谊的期许和信心,一点点地消磨,曾经觉得是那么近距离和相互支持依靠的关系,一点点地在消亡死去。
我在一次次的相处里看到,我们的步伐和面对的生活课题,有着很大的差距。在缘分的走向里,我们不同城市的差异,客观地摆在那里。因为常联系,我很了解,非常理解她最近工作压力大,而她一贯以来的连轴转,经常是需要我提醒她快停一停,她确实没有余力。我因为了解,所以理解。
但是我不原谅,我不原谅这种给过承诺后的抛弃,和在关键时刻她人不在场的背离。
也或者说,我的「失望」「无语」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失去沟通的想法,我放弃。我真实地面对自己,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隐约意识到,但是没有对自己完全承认,在更早于当下,这一个旧的我的生命整个在崩塌和破碎的时候,她已经看不到或者说看不清我的生命主线课题。
我一直是相信「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但我也很理解,现实生活就是会有很多机缘的不确定,关系会因为不可抗的原因走向分离。我们还会是朋友,或许说,还可以是朋友,是可以在有机缘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是可以交流的,但是我们的关系回不去从前了。过多的期待,会让关系超载,归零的期待,会终结关系的定义。
这是一段在生活里被迫,在自由意志上主动的友谊降级。浪蔓的诗,这一篇章终要落地,走向一个更加「正常」的结局。我不会再对她释放那么多我的分享欲,我点滴的情绪,细碎的成长和镇痛后的体悟,也许会分散给其他人,也或许我再也不想和谁分享,也许我以后会更多对着湖面和树木,对着落日和微风倾诉。
这一篇的诉说或许是哀悼过往关系的逝去,也或许是一个面对自己的自我梳理,也可以是一种人生经历的一个小小笔记。我感恩她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陪伴和支持我一起,我们度过的许多大的小的时刻,重要的瞬间。在彼此生命曾经紧密的交集里,我们照应和镜映出的对方和自己,真切经历过的共处的一切情绪、感受和经验,都会在我接下来的人生,或遗忘或铭记地存在着。
我会继续地爱着和祝福着,她的固执牛脾气,她的自我小情绪,还有她笑起来的眼睛笑眯眯。在心里持续地浅浅地祝愿,她在我之后,也会遇到很好的人,给她更多的对很多事情的信心,一步步的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允许和松弛。我们都是很努力和美好的人,我们都会有适合自己的同行者,会有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也会有陪在我们身边,为我们闪耀的星辰。
这是本文开始写作的第二天,我在听着华晨宇的《不重逢》。她突然打视频过来,我们联络对话了。我发现自己很平静,心里对她真的没有太多的起伏。曾经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至交好友和亲人,在我的意义世界里,我们的彼此承诺所赋予对方的,是家人一般的位置,现在我把她归回为好友,回到朋友的位置。
曾经的我,面对我一个人就是我的家,是无法承受这样的现实的,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的孤独感时常让我恐惧。那个我的内核,是不足以支撑承认和面对这些的,但是现在翻过了很多的山,一个人穿越了新的更庞大的黑暗山谷,我现在依旧在步履蹒跚,跌跌撞撞,也带着害怕和忐忑前进,但是我可以承认和迎接这样的人生了。以后还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需要和朋友,和不同的人连接的时刻,以及我需要他们的短暂瞬间,我愿意连接,我也接受离别。经历这一段关系,它的起承转合,我们彼此奔赴,被对方的刺扎到后依旧奔向对方的时刻,弥足珍贵,被看见和被接住过,以及我付出过的爱的感受,都在我的生命留下印记,将陪着我继续这充满未知和不确定的生命。感恩生命,感谢相遇,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各自的,彼此为对方喝彩的未来。
榴莲大龙猫
(因篇幅有限,信的内容略有删节)

图源剧集《正常人》
(接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