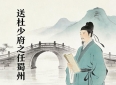*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新刊出炉!点击上图,一键下单↑↑↑
「女性友谊」
不久前结束的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仪式上,电影《好东西》成为最大赢家,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这部讲述女性友谊的电影让很多年轻女性感同身受,也让女性友谊的话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以郑重姿态来声明自己“拥有友谊”。她们打破由亲密关系隔绝出的“孤岛”,或者在网络的遥远声援中,或者因共同的困境建立起女性联盟,最终这让她们获得了对抗迷惘的力量,实现自我成长。
记者 | 吴丽玮
摆脱“孤岛”
当编辑跟我谈女性友谊这个封面时,我一开始是懵的。谁都有朋友,也都在友谊中受过益,友谊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但是电影《好东西》、小说《我的天才女友》等等讲述女性友谊的影视文学作品如此受欢迎,又似乎说明了女性友谊变得比过去更加重要了。

讲述女性友谊的电影《好东西》 成为第 38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大赢家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纪莺莺做过一个上海老年合唱团女性友谊的田野调查,“如果我去跟别人讲中老年女性群体的研究,大家也会说这是一个‘girls help girls’的故事。”纪莺莺说,她发现老年女性不会把友谊当做一个严肃问题来看,“她们会说,‘我们退休了,在合唱团认识了几个好朋友,很开心’,她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现在年轻女性会用一种很郑重的姿态来声明自己:正在‘拥有友谊’。”
我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一个“全女家庭”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两个离异带娃的女性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和事业上的合作,她们组成了一个家庭,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其中一个妈妈告诉我,当她们2023年第一次发生活视频时,因为当年有一个网络热词“离婚搭子”,所以她们的视频一下子就火了。第二年当她们再被人提及,“离婚搭子”又变成了“养娃合伙人”。今年她们准备做一个垂直的账号,专讲生活,“结果因为今年有‘全女家庭’这个话题,新视频又火了。每一年的流行语会变,但是我们这样的组合一直都被很多人关注。”

插图:范薇
但真正让我能够理解友谊为什么对当代中国女性这么重要,是通过寻找“女性友谊”这个概念的过程。
我们会觉得友谊是个很古老的话题吧。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友谊是“一个灵魂寄居在两个身体里”。蒙田的随笔《论友谊》也是历史上描述友谊的经典作品。但这些歌颂,通通与女性无关。美国性别研究学者玛丽莲·亚隆在《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一书中写道:“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女性友谊一直持否定态度,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脆弱’,天生不配拥有最高层次的友谊。”
真正的女性友谊的概念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可能晚到你无法想象。直到半个世纪前的世界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时期,才开始有女性主义研究者提出了属于女性的友谊概念。1970年代,美国女诗人罗宾·摩根出版一本文集《姐妹情谊就是力量》,“姐妹情谊”(sisterhood)开始成为女性友谊的一个代名词。

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讲述了两个贫民窟女孩的友谊故事,为女性的友谊关系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模板
“姐妹情谊”的内涵可以结合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时代背景来理解。1963年,美国女性运动领袖贝蒂·弗里丹出版著作《女性的奥秘》,成为了这次女性运动浪潮的一面旗帜。弗里丹在书中讲述了当时美国郊区家庭主妇的困境,她们看起来是被“全世界妇女所嫉妒”的“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但在这种舒适和惬意的生活方式背后,美国女性正在经受“无名问题”的困扰:空虚、疲惫、绝望、不满等等。弗里丹指出,在性别歧视与压迫的社会大环境之中,女性的命运不能仅仅维系在婚姻和家庭之间,女性要发展事业,只有这样才要争取到与男性一样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1968 年,美国女性运动领袖贝蒂 · 弗里丹(左二)与女性主义活动家们在交谈(视觉中国 供图)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谢晶看来,女性友谊就是在打破“孤岛”后结成的一种共生关系。“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中,女性是被孤立的,因而很难在彼此之间建立友谊。”谢晶分析道,在封建社会里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讲的是阶层和门第”,而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以自由和专一的爱情为前提的婚姻成为一种理想,“在近代小说以及现当代的影视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对于这种理想爱情的呈现,人们,尤其是女性,开始把亲密关系放在所有关系之前,再加上家庭的原子化,这一切都使得女性之间原本非常稳固的情谊慢慢被削弱,甚至被切断。困于家庭中的女性是一座座‘孤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谢晶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渴望摆脱“孤岛”,与世界建立更多联结(受访者供图)
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正在意识并试图摆脱“孤岛”,谢晶在大学校园里感受到这种变化趋势是非常迅速的。“依然有很多学生感觉到亲密关系很重要,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开始意识到,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获得幸福感的手段,并不仅仅只能靠亲密关系,或者是通过组建一个家庭。她们也意识到,两性赋予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往往有巨大的区别。男孩子有很多幸福感和价值感的获得方式,在恋爱中,女孩往往比男孩要更投入,也更容易患得患失。这与整个社会希望女性扮演的角色息息相关。很多女生在这一类意识觉醒之后开始寻求与外界建立更广泛和多样的连接。”
在困境中结盟
在电影《失恋33天》里,女主角直到失恋很多天之后才意识到:我还拥有一大帮好朋友。男女对待爱情的态度反映着从小经受的性别差异教育。“男孩从小就会被教育说要出人头地,他们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只要事业强大,自然就会有女孩喜欢你’。但是女孩往往从小会被教育要温柔善良,家庭对女孩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位心理咨询师这样跟我分析道,“所以当大学生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发现男孩受影响比较小,他们该学习学习,该跟自己的好朋友打球就去打球,但是女孩会把爱情看得很重,甚至是唯一。”

电视剧《失恋33天》剧照
在这种性别差异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分工不同,导致女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关系长期遭受父权社会的贬低和污名化。
“从‘原始’社会中的性别分工开始,女性就以‘照料和修护’为主要活动,男性的活动则以建造为主,甚至是破坏和杀伤式的。”谢晶分析道,女性的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被归为“再生产”的一部分,她们的价值是不被认可的。比如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里讨论什么样的活动是重要的。一个马克杯,它被生产了一次,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它在生产出来之后反复被弄脏,反复被洗。“这是典型的女性在做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就被认为没有生产和创造,因而没有价值。”谢晶说。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典型的兄弟情谊(brotherhood)是权力和等级关系,“男性友谊建立在理性协商、分工以及明晰的权利义务之上,常常有‘共同事业’这样的明确目的。”谢晶说道,而专注“照料和关怀”的女性之间的情谊则是无阶序的,并且是情感导向的,这样的情谊在父权社会中得不到重视,它总是被形容为“没完没了的闲聊”、“八卦”和“幼稚”。“实际上,女性友谊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没有彼此的不断竞争和评估,它是一种陪伴、照料之上的情感与关怀共同体。这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和抚慰人的心灵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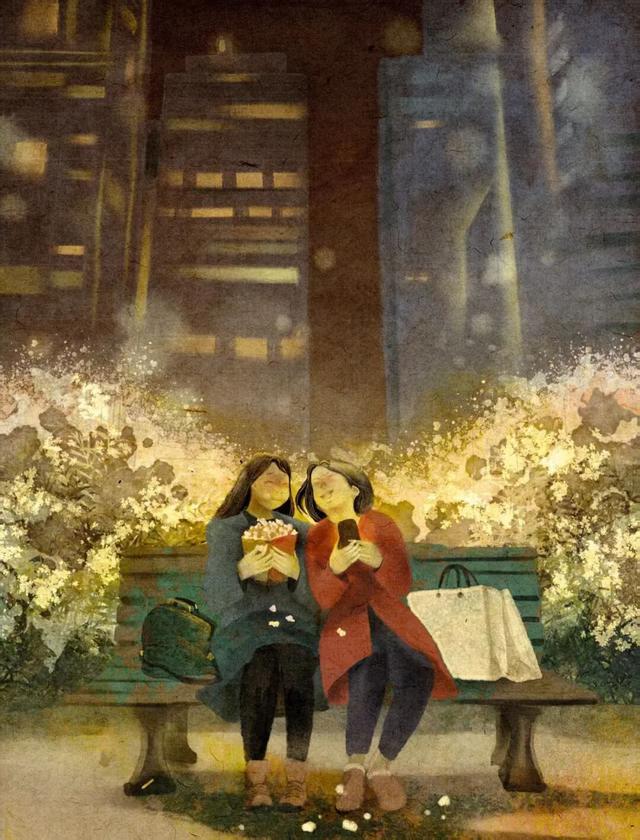
插图:范薇
这样的情感共同体对于处于不利境地的女性来说尤其重要。
201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参与了教育部一项关于高端女性人才成长的课题研究。“现在大学的入学率男女相同,如果把大学看作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方式的话,未来几十年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发展应该是一样的。但事实大家都知道,在职场的金字塔结构中,站在塔尖的女性是远远要少于男性的。我们当时的研究就是要去解释为什么女性被‘甩’出去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希望各领域中的女性都可以形成 一种相互支持的体系(蔡小川 摄)
佟新告诉我,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很多因素,但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女性很难像男性那样建立自己的情谊关系网。“比如我们学校物理学院的女教授,已经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了,但也会说,如果是几个研究物理的、计算机的、数学的男教授,他们很容易就能聚在一起,吃一顿饭就促成一个项目的合作关系。但这对女教授来说太难了。在学术环境里如此,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所以我总是跟我的学生讲,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姐妹会’,在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支持体系。”
女性正在被男性排斥的领域里建立越来越多自己的支持体系。比如全女形式的户外登山组织的建立,是源于女性对于身处户外领域劣势位置的深刻体会。
去年6月,一家户外机构组织的一次北京徒步活动发生了事故,50多名女性组成的队伍跟着男领队一起在山里迷路,走了12个小时,直至晚上11点才得以返回。原本是对于事故的讨论,只因为一位女队员在下撤过程中瑜伽裤被磨破的照片而转变了舆论风向。这张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后,女队员们被一些人讽刺为“穿着吊带和瑜伽裤爬山的小仙女”和“登山媛”,此后网上的舆论逐渐发酵成了对女性登山者的嘲讽。
这让很多人意识到,女性在户外圈里所要遭受的歧视甚至是痛苦:男性凝视,言语甚至是肢体骚扰等等。而全女户外俱乐部的成立则让很多女孩感受到这个项目纯粹的愉悦感:“大家会互相理解体能上的差异,也不用去忍受身体上的不舒服。线路规划、天气预案都会做得很细,也会详细告知队员需要携带的物品。”
佟新觉得,包括女性户外在内的女性装修队、全女酒店、女性健身房等等女性支持模式与网络和自媒体不断发出的女性声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们过去的教育过程里,女孩是没有被鼓励去正面表达情感,去表达不满和愤怒的。小女孩对某个朋友不高兴了,就是一瞪眼,一天不理她,用冷暴力来惩罚对方,这成了无论东西方女孩的一种普遍交往模式。”
佟新说,但她在近几年感觉到数字平台的多样性发展正在构筑着新型的女性文化,“‘小宇宙’上的女性播客、女性脱口秀演员的段子,各种社交媒体上的经验分享等等,网络的匿名性也使得跨时间、跨空间地对女性表示支持变得非常容易。这个力量特别强大,女性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成了‘第一性’的言说主体,而不是被男性讲述。女性现在更容易实现共同体的结盟了。”

包括女性脱口秀在内的新型女性文化让女性可以直接表达态度,成为“第一性”的言说主体(视觉中国 供图)
就比如一个全女户外组织小红书账号上置顶的一篇帖子,讲的是她们在登山过程中互相配合,在野外上厕所。“以前我在登山过程中总是看到女孩因为不方便上厕所,或者害怕落下队伍,一直要憋尿憋到下山,我不希望女孩要额外承受这些痛苦。”组织创始人告诉我,这条帖子获发布之后得了约7万个赞,以及超过7500条评论。在评论里,女孩们隔空分享着自己在各种各样的户外情景里上厕所的故事。
成为自己
在《女士交谈:建构女性友谊的话语》一书中,作者詹尼弗·柯茨将女性友谊的两个组成元素总结为:相互支持和能“成为你自己”。“她们经常用互相理解这样的字眼来表达那种感到被接受的感觉,朋友就是和她在一起时你就完全成为你自己。”
“当一个人迷茫、失落,甚至感觉到受伤的时候,需要的是有个人在她快要倒下的时候能够托住她。你可以什么话都不要讲,只要在她寻找关注的时候看到她,在她哭的时候抱抱她,听她把苦水吐完,这种友谊就已经起到很大作用了。”谢晶说道。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对于年轻人来讲,承托的角色原本应该是家庭扮演的,谢晶说:“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已经不再这么做了。他们对孩子是很苛刻的,不断地评判孩子,也为孩子安排好一切。作为老师,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上位者,太容易去指摘学生了,老师自以为拥有让学生变优秀的方法,看到学生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变好,就会很急很严厉。孩子在双重的挤压下长大,进入大学或者工作了以后,他们离自己的原生家庭非常远,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走自己的路,变成一个很孤单,内心又很空的状态。”
武汉理工大学职业发展中心副教授张晓文在学校开设一门广受学生欢迎的“爱情心理学”课程,同时她也为在校生做心理咨询。“如果你想改变原生家庭对你人格的塑造,那你一定要与社会建立起新的连接才能动摇它。”张晓文告诉我,这些连接中包含深刻的亲密关系,未来会组建的核心家庭关系,当然也包含友谊。
“现在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的问题上是有很大困扰的,他们存在一种‘人际贫困’的问题,于是自我也很难得到发展。”张晓文说,她会优先让学生去发展友谊,“友谊是在大学阶段能够建立起来的一种最好的关系。相比被动接受的亲情,友谊是主动去建立的,它具有独立性,也具备边界感。友谊包含着包容、互惠等很多内容,建立友谊本身就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张晓文说,建立友谊是重新成长的第一步,接下来她也鼓励学生在友谊的基础上去发展出爱情,“这样的亲密关系会更持久,会有更多话题”。

电视剧《欢乐颂》剧照
当代年轻人正日益延缓其承担成人角色的社会年龄,一份好的友谊或许可以给予他们呵护和滋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心理成年的机会。
我采访了两个在一起相处10年的女孩,她们从大学毕业后直到现在30多岁一直在一起合租房子,两人一起做过微商卖面膜,后来又先后到健身房当教练,并合作开了自己的健身工作室。去年两人决定放下一切,搬到大理生活,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
两人保持友谊关系的秘籍,可以说是因为她们从未锁死彼此的这段关系。她们各自恋爱,曾经接近过婚姻,也去相过亲,把自己和对方的条件都摆在桌面上盘算。她们也跟其他女性之间建立过各种友情,尤其是健身工作室里,当她们帮助女性解决身材焦虑和调整生活状态时,彼此暴露和承接脆弱一面的过程,使她们跟很多会员发展成了日后不断联络的好朋友关系。
而当时间来到30岁后,两人在疫情期间跑到大理躲避封控,忽然意识到原来生活是可以自主选择的。二十几岁时计划去结婚,互相比较着婚姻的条件,这是自己想过的生活吗?不过是按照社会时钟的运转,被推着走而已。她们俩在电话里快乐地告诉我,已经想好了,彼此的陪伴就很好,未来可能不会走进婚姻。

Cici(左)和 Mia(右)已经认识了 10 年,在彼此的陪伴下,她们开始审视人生该做的选择(受访者供图)
在获得支持,得以重新梳理人生方面,女性比男性的处境要好得多。“父权社会允许女性向朋友诉苦,用友谊去对抗这种虚无。”谢晶分析道,但是男性就没这么幸运了。“在那些符合父权制要求,从而获得很多好处的男性之外,还有一些男性是对从小就开始的‘雄竞’不适应的,他们可能在小时候就遭受到霸凌,开始反思这种相互竞争的模式,但是他们想获得一个能够示弱,能够接纳他的负面情绪,缓解冲突和迷惘的男性友谊关系非常困难。”
“其实我一直强调在男性之间也可以建立情感的共同体,就像在女性之间也会有权力关系和‘摆事实、讲道理’的理性商议关系。这些都是不同的关系类型,只不过对于姐妹情谊的污名化和对于女性的孤立,使得我们现在常常要重新找回那种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不带评判和不分你我的情谊。”谢晶说。
我们欢迎男性加入我们的姐妹情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