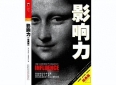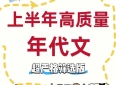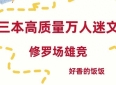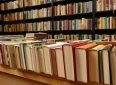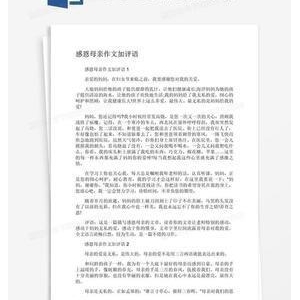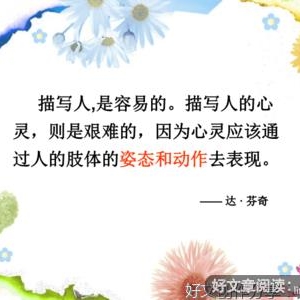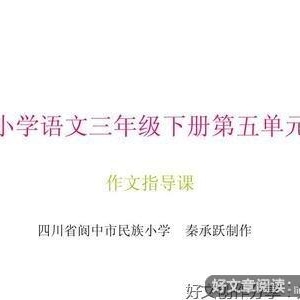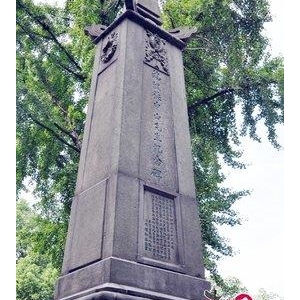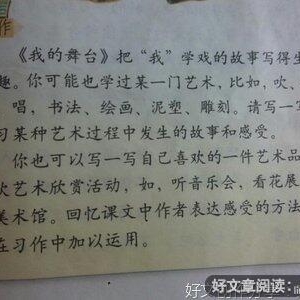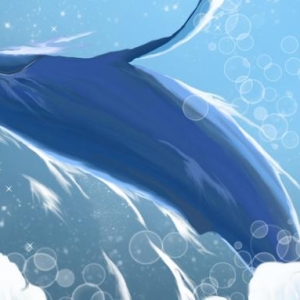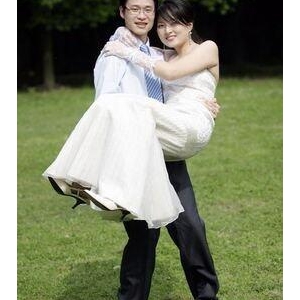1
最近读了好几本美食方面的书籍,有些偏重发表评论,有些偏重阐释文化,要论最好吃的,非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莫属了。
真爱美食的朋友,着实应该好好读一下汪先生的散文。但转念一想,或许也不该读。说应该读,是因为散文中的每一个句子,都写得垂涎欲滴,让人欲罢不能。说不应该读,是因为看到妙处,你肯定就得花钱,要么是买食材要么是点外卖,必然增加你的消费开支,哈哈。
上述观点,不是我的“独到”见解,豆瓣上每一个看过汪曾祺先生美食散文的网友,都这么评价。
在接受《十三邀》采访时,《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说:别的作家写的美食,他都看过吃过,但没觉得好吃。真正感受强烈的还是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他写的那些,都是我们每天能在家里碰到吃到的。汪先生让他知道了,其实在家常便饭中,都能找到美食的影子。
而《舌尖上的中国》这些美食纪录片,正是秉持了这样的传统,将汪曾祺先生的书面文字平滑地切到影视这个新文化载体,才获得了这么巨大的成功。

2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特别擅长使用短句,而且句子之间的气口衔接得非常完美,所以阅读体验如行云流水。但这么好的文字,写读书笔记会有很大的难度。按理说,读书笔记应当写自己的读后感悟,用自己的话进行表达。但放着汪先生那么好的词句不用,另起炉灶炒冷饭,想想也是极煞风景的。
先来个狮子头,看能不能让你口舌生津:猪肉肥瘦各半,爱吃肥的亦可肥七瘦三,要“细切粗斩”,如石榴米大小(绞肉机绞的肉末不行),荸荠切碎,与肉末同拌,用手抟成招柑大的球,入油锅略炸,至外结薄壳,捞出,放进水锅中,加酱油、糖,慢火煮,煮至透味,收汤放入深腹大盘。
以上描述是不是简洁明了、鲜活生动?虽然用字不多,但你完全可以对照着行文,按部就班地把狮子头给做出来。而且单看制作步骤,你就知道必是美味佳肴跑不了。

3
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当地的知名美食咸鸭蛋,令他引以为傲。用他自己的话说:“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汪先生描写咸鸭蛋的句子,也是难得的精彩: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类似“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种形象化的表述,用词极简,表达又极准。既能让你对这文字爱不释手,又能让你对文字描绘的食物爱不释手。

4
有一次,北京的老同学请汪曾祺先生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顺带还用激将法问他:“你敢不敢喝豆汁儿?”
汪先生很有趣,提出了他的四大不吃理论: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
然后跟同学说,就喝个豆汁,有什么不敢?
同学再三警告:“喝不了,就别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
没想到汪先生端起碗来,几口就喝完了。
同学便试探性地问:“怎么样?”
汪先生说:“再来一碗。”
当然,汪曾祺先生也有招架不住的食物,他曾经在文章中说: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有些吃的我也招架不了,比如贵州的鱼腥草)。
汪先生在这里想表达的,绝对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种对文艺工作者的期许——要能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另外,汪先生还通过食物类比: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汪曾祺先生主张用包容开放的态度,看待各式各样的文化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

5
有人问汪曾祺先生,你写的这些美食散文,又不算系统的食谱,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汪先生只说了这么一句: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许知远曾经问陈晓卿:“如果汪曾祺先生看到你拍的美食纪录片,会是什么感觉?”
陈晓卿幽默地答复:“汪先生说,里边偷了我不少字句。比如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便是最美好的意境。
每当感到疲惫的时候,看一眼汪先生写的这些美食文字,或许能更进一步,在温馨的灯火之下做点吃食,这便是热爱生活的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