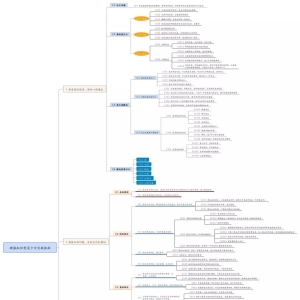散文:《一个人死了》。
作者:宋增强。
榆树还那样站着,在深冬里显得格外嶙峋,叶子早已落尽,只剩下些倔强的枯枝伸向铁灰色的天空,像是想要抓住什么,终究什么也没抓住。树皮冻得更加皲裂,那千万道纹路此刻看去竟像极了邻居奶奶手上那些冻疮愈合后又裂开的口子。
我忽然记起他的话,那是某个同样寒冷的冬日,我们围着他小小的碳盆,他拨弄着火灰,轻轻地说:这老榆树心里明白着,一个人走了,他的枝子变脆了一分。那时炭火碧波作响,映着他慈和又有些模糊的脸。如今这话伴着盆火的暖意一同从记忆深处浮起来,却浸透了眼前的寒气。

巷口传来锯木的声响,涩涩的锯着凝动的空气是李木匠,他呵出的白气在他佝偻的身前聚了又散。这个背已弯成一张冻僵的弓的外乡人正对付着那些比平日更显坚硬的柏木。他的耳朵冻得通红,上面仍别着那只两头削尖的铅笔,像个固执的旧标签。人们都说他不用听也能知道谁家有了白事,是冬日的空气里有一种特别的沉寂。

会找到他,他刨着木头,爆花在冷风中脆弱的卷曲,不像夏日那般柔顺,落下时也无声无息。他口中仍念叨着"船舶",那陌生的口音混在白色的呵气里飘向着北方村庄。干冷的天空,这船要在冻土开裂前造好,好载着人航向那无人归来之港。

亲人们从寺下里赶来,带着一身的风雪气聚在燃着煤炉的屋里,商量着白布的尺寸,墓穴该如何在那铁板一样的冻土上开挖,鼓乐班子在冷天里的价钱是否要添些。他们的声音压得低,话语简短,偶尔被窗外一阵尖利的北风打断,而逝者留下的温热痕迹正被这深冬迅速吞没。
羊圈早就空了,石槽里结着浑浊的冰,菜园子被一场薄雪敷衍的盖着,露出底下枯黑的梗茎。那只聒噪的大鹅如今瑟缩在檐下,它下一个蛋。在这彻骨的寒冷里,该放在哪里才能保住些微的暖意呢?生活里那些细碎的熟悉的节奏,随着主人的离去戛然而止,比季节的变换更为决绝。

最让我心头一揪的还是那只银镯子,从老人腕上退下时,想必触感是沁人的凉。那几十年来被体温捂得温润的光泽,似乎也瞬间暗淡了些。他会被怎样处置呢?是套上另一个年轻却同样操劳的手腕,还是投入炉火,化作一滴类型的银水,再铸成一把守护新生的长命锁。

物质的传递如此具体,而生命的温度却在这一递一接之间悄然改换了。冬日的天黑得早,木匠的船造好了,停在堂屋中央,泛着新木的清冷气味。女眷们的白布在灯下,显得愈发的白,刺目的白。我踱回榆树下那只失了依托的乌鸦,终于落在最高最秃的一根枝丫上,缩着脖子,像一团凝结的墨块。

他叫不出声了,或是叫声被厚重的寒冷吸了去。一个人死了,在这初冬,他的呼吸与体温消散的似乎更快,像呵出的一口气,转眼就没了踪影。可他的离去,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砸进这冰封的生活水面。冰面震动了,裂开细密的纹,波及到羊圈、菜园。慌乱的鹅,波及到木匠的浮凿、亲人的忙碌、一件银饰的漂泊。
原来,一个人的谢幕从不是孤寂的转身,而是冬日里一声沉重的闷响,让整个与他相连的世界,都跟着簌簌的颤抖了一下。我伸手摸了摸榆树,冻得硬邦邦的树皮,冰冷硌手。他还会在这里站着,度过许多个比这更严酷的冬天。看着更多的窝在风雪中散落,听着更多的船舶下水,他什么都知道,却只是沉默,在风里摇晃着枯硬的枝桠,发出呜呜的声响,把所有的告别与心声,都深深的藏进他脚下那片被冻僵的泥土里。

别忘了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