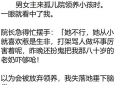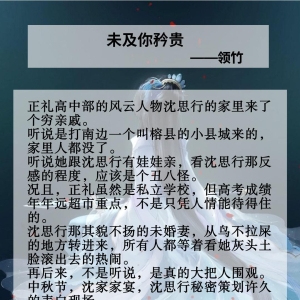文/任天义:苦日子里的姐弟情
——黄土塬上一段难忘的亲情往事
人这一辈子,走过多少路,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到老了,最难忘的,还是年轻时那些掏心掏肺的亲情。我今年岁数大了,闲下来就常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闭眼,几十年前的事儿就跟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眼前晃。
那时候穷,苦,难,啥都没有,可人心实,亲情重。姐姐一家遭难,我们兄弟三人,拼了命也要帮一把。种地、收麦、背粮、磨面、拉娃看病、跑乾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苦水里泡出来的真情。
这些事儿,没人给我记,我就自己讲出来,留给后人,也留给自己。苦日子过去了,可这份情,一辈子都不能忘。
第一章 姐夫远走临夏,姐姐一人扛起一个家
姐夫孙佩琦年轻的时候,被组织上统一分配,去了遥远的临夏工作。临夏离我们老家白莲湾太远太远,那时候交通不便,不通车,路难走,姐夫一去,一年半载都回不来一趟。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完全指望不上他。
姐夫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二伯,还有二妈,那时候年纪都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老两口常年病痛缠身,走路费劲,干活无力,家里的重活、累活,一点都搭不上手。日常吃饭穿衣、端水熬药、洗洗涮涮,全都得有人守在跟前伺候。
姐姐嫁过去,就成了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唯一的依靠。她一边要照顾年迈多病的公公婆婆,一边还要拉扯自己的小女儿丑女,日子过得难上加难。
那时候还是大集体生产队时代,家家户户必须参加集体劳动,靠挣工分才能分到粮食。不去劳动,就没有口粮,一家人就得饿肚子。姐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生产队下地干活,锄地、拔草、施肥、收割,风吹日晒,从早忙到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可就算在生产队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家,她还是不能休息。要给二伯二妈做饭、喂药、铺床,要照顾年幼的女儿,要喂猪喂鸡,要收拾屋子,常常忙到深更半夜,油灯点了一盏又一盏,人却连一口热汤都喝不上。
我们兄弟几个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姐姐一个女人家,再坚强也有撑不住的时候。我们商量好:姐姐难,我们当兄弟的,就必须站出来,替她扛!
从那以后,我们兄弟三人,就成了姐姐家最固定的劳力,再苦再累,从来没有退缩过。
第二章 白莲湾的田地,兄弟三人春种秋收不停歇
姐姐家在白莲湾,庄子前面、庄子后面,有好几块自留地,那是全家活命的根本。那时候没有拖拉机,没有播种机,没有收割机,所有农活全靠一双手、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点一点干出来。
每年春天,土地刚一解冻,我们兄弟三人就扛着农具来到姐姐家。翻地、耙地、施肥、播种,一步都不马虎。别人家里有男人做主,姐姐家没有,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她家的顶梁柱。
到了麦收季节,地里一片金黄,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烫,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流到嘴角又咸又苦。我们一人一把镰刀,天不亮就下地,割麦、捆麦、拉麦、碾场、扬场,一套活儿干下来,人能脱一层皮。手上磨出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结成厚厚的老茧,摸上去硬邦邦的。
秋天一到,又要忙着种秋、收秋。玉米、黄豆、高粱,种的时候要弯腰点籽,收的时候要用力搬运,晒粮食要守着天气,怕下雨,怕刮风,怕粮食发霉坏掉。白莲湾前后所有的田地,一年又一年,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全都是我们兄弟三人包下来。
村里人见了都夸:“你姐姐有你们这三个兄弟,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我们听了不说话,只知道一句话:姐弟情深,打断骨头连着筋,她难,我们不能不管。
第三章 没电的岁月,人推石磨磨不尽的苦
那时候最艰难的,还不是种地,而是磨面。
村里根本没有电,更没有电磨、粉碎机。家家户户吃的面,全靠最老最笨的办法:石磨子,人推着磨。
一方大石磨,放在院子里,上扇压着下扇,中间插一根木磨棍,人抓着磨棍,一圈一圈往前推。粮食倒进去,慢慢磨成粉,磨一遍不够细,还要用罗筛,筛完再磨第二遍、第三遍。
推磨是最熬人的活。转得人头晕眼花,腰酸腿疼,胳膊抬不起来,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姐姐要照顾老人孩子,根本没有力气天天推磨。于是,磨面的活儿,又落在了我们兄弟身上。
一有空,我们就去姐姐家帮忙推磨,有时候一推就是大半天,从太阳高照,推到夕阳落山。看着磨盘里一点点流出来的白面,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姐姐一家能吃上馍、吃上面条,再累都值。
那时候的粮食金贵,每一粒都是汗水换回来的。石磨转一圈,苦日子就好像长一分,可亲情,也在这一圈一圈的转动里,越来越深。
第四章 干河水磨建成,背粮排队磨面受尽苦
后来,村里传来好消息:白莲湾下边的干河,建起了一座水磨。靠河水冲击轮子带动磨盘,比人推快一点,也省一点力气。
消息一传开,十里八村的人全都背着粮食往河边跑,队伍排得老长,从河底一直排到半坡上。去晚了,当天根本排不上,只能在河边等一夜。
我和二哥任天寿那时候年纪还小,身子骨没长结实,却要背着沉甸甸的麦子,从姐姐家一步步走到干河底下。山路又陡又滑,肩膀被布袋勒得通红,疼得钻心,走几步就得歇一歇。
到了河边,先排队,等磨盘,等粮食磨成面。有时候头一天下午就去,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轮上。整夜就在河边蹲着、坐着,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几口河水,困得眼皮打架,也不敢离开,生怕排的号丢了。
面磨好了,更难的还在后面:从河底往坡上背。
一步一挪,背一歇三,浑身大汗淋漓,衣服湿透,贴在身上又冷又黏。腿发抖,心发慌,头晕眼花,好几次都差点栽倒在坡上。那时候我最怕磨面,不是怕累,是怕那股压得人喘不过气的重量。
可一想到姐姐在家等着面下锅,老人孩子要吃饭,我咬着牙,也得一步一步往上走。
第五章 杨家河钢辊磨更快,路更远背粮更难
干河的水磨磨得慢,排队太久,实在熬不住。没过多久,我们又听说,离干河不远处的杨家河,也建了一座水磨。
这座磨不一样,不用石头磨盘,改用钢辊、钢皮磨,和后来的电磨差不多,磨得又快又细,效率高很多。我们一听,立马改去杨家河磨面。
可路更远,坡更陡,粮食还是要靠人背。
我和二哥,一人扛一袋粮食,小小年纪,腰都压弯了。路上尘土飞扬,太阳晒得人脱皮,汗水流进眼里,涩得睁不开眼。一路上,两个人互相搀扶,互相打气,谁也不说一句苦,谁也不喊一声累。
到了地方,依旧要排队,只是比干河快一点。磨完面,再背着面往回走。那些年,我们背过的粮食能堆成山,走过的路能绕白莲湾无数圈,流的汗水能把土地浇透。
一切,都只为姐姐一家能吃上一口饱饭。
第六章 丑女从小多病,我们背娃推車跑遍医院
姐姐的大女儿叫丑女,不是长得丑,是乡下人为了孩子好养活,特意起的贱名。二伯二妈得孙辈迟,全家人把丑女当成心头肉,可孩子从小体质弱,经常害病,三天两头发烧、咳嗽、肚子疼,一病就蔫蔫的,让人看着心疼。
姐姐要上工,要照顾老人,走不开。带丑女看病的担子,自然又落在我和二哥身上。
杨峪地段医院,离村里有很远一段路。没有车,没有自行车,我们只能背着孩子走。我背着,二哥跟着,一路哄,一路劝,怕孩子哭,怕孩子闹,更怕病情加重。山路坑坑洼洼,一来一回就是小半天。
有一次,丑女病得重,我推出家里的单轮木车,把孩子轻轻放在车上,小心翼翼往医院推。路不平,车不稳,我不敢快也不敢慢。回来的路上,孩子耍小脾气,不愿意好好坐,一会儿哭,一会儿闹,我们又哄又劝,慢慢悠悠,折腾好久才回到家。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虽然苦,可心里踏实。我们多跑一趟,姐姐就少操一份心;我们多受一点累,孩子就能早一天好起来。
第七章 一年忙到头,农活家务样样都帮
那些年,我们兄弟三人在姐姐家帮忙,从来没有分过你我,也没有算过得失。
春天犁地播种,夏天收麦碾场,秋天收秋种麦,冬天拾柴修农具。家里的重活、脏活、累活,我们看见就干,从不推脱。白莲湾的每一块地里,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每一棵庄稼里,都浸透过我们的汗水。
我们不图吃,不图穿,不图回报,只图姐姐能少受一点苦,这个家能平平安安。村里人都说我们太实在,可我们知道:亲情,不是用来算的,是用来做的。
第八章 姐夫调回家里刚稳,丑女再次病重
苦日子熬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姐夫孙佩琦,从临夏调回来了!
姐姐终于有了依靠,家里终于有了顶梁柱,我们兄弟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一半。可谁也没料到,刚安稳没几天,丑女突然又病重了。这一次比以往都厉害,吃药打针不见好转,村里医生不敢耽误,让赶紧送到乾县县城大医院去看。
那时候去乾县城,比现在出远门还难。没有汽车,没有班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架子车。
我和大哥二话不说,套好车子,铺上被褥,让姐姐抱着丑女坐上去。我们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面推,一步一步,踩着黄土路,向乾县城走去。路不平,车颠簸,我们不敢快跑,怕颠着孩子;也不敢太慢,怕耽误病情。
一路上,渴了喝凉水,饿了啃干馍,汗水把衣服浸透了一遍又一遍。
第九章 第一次进乾县城,亲眼看见政法组大机关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真正走进乾县城。街上人来人往,房子整齐气派,对我们一辈子在山沟沟种地的人来说,一切都新鲜又陌生。
我们一路打听医院,在路上,亲眼看见了县政法组的大机关。大门庄严,院子干净,楼房整齐,我这辈子从来没进过公家的大机关、大单位,连县城都很少来。这一次为了给丑女看病,不仅进了城,还见到了政法组这样的大地方,心里既紧张,又感慨。
那时候我就在心里想:再苦再难,只要一家人一条心,总有熬出头的一天。
我们顺利给孩子看病、拿药,丑女的脸色慢慢好转,姐姐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完病,我们才简单逛了逛乾县城,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进城。
第十章 苦尽甘来,亲情永远记在心间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日子和以前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电了,有磨面机了,有车了,看病方便了,出门也快了,当年的苦日子,一去再也不回。
可我永远忘不了:白莲湾的黄土坡,干河的水磨,杨家河的钢辊磨,架子车颠簸的山路,背上沉甸甸的粮食,怀里生病的娃娃,乾县城里的政法组机关,还有我们兄弟三人,为姐姐一家流过的每一滴汗。
那时候啥都没有,只有亲情。
再难,再苦,再累,一家人互相帮衬,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这些事儿,我讲给后人听,不是为了夸自己,是想让他们知道:
日子再好,不能忘本;
亲人再远,不能忘情。
苦日子里的姐弟情,是我这辈子最珍贵、最难忘的宝贝。
乙巳年腊月 作于乾县顺太街家中